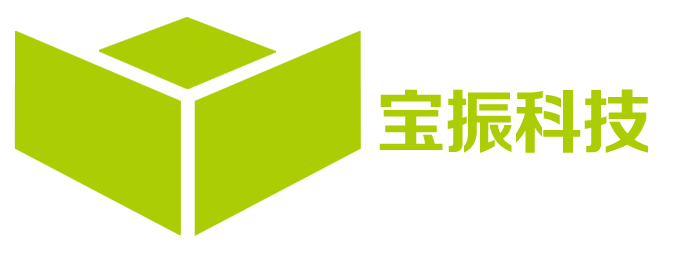刚才袁运甫教授的发言中阐述了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艺术作品展所要体现的“和而不同” 的主题和他一贯倡导的“大美术”观,指出艺术设计无论大小,都应该为社会服务;无论艺术家的作品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一个设计师,哪怕做一个很小的东西,没有一个大的视野,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有意义设计来。本人非常赞同,借题发挥,我想谈谈这个“和”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这个大的视野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充满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手口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原本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它促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理性与人性的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类似意义上的”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欧洲独裁主义者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Winslow,1999)。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八十五年前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 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 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设计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其它学科和文化领域所不能替代的。从蔡元培倡导的美育作为树立健全的人和理想社会之途径,到丰子恺先生当年的“只要有艺术,国家就不会灭亡的艺术救国信念,再到近年来袁运甫、陈逸飞、陈邵华等艺术设计大师们倡导的“大美术”和“设计立国”,都在向当代艺术与设计同仁昭示,设计学科需要有关于社会、国家和“大写人”的大视野,而这个大视野便是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危机。
1 大视野之一: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梁启超,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文化认同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
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体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张汝伦,2001)。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文化认同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手口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Seamon,1980)。如果说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Cosgrove,1984),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二百年以前或者一百五十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鲜明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乾隆大帝,认同于康熙大帝,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设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04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和军事设施。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作为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文化认同的危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组合种植花箱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时代发展到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一次凸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包括对新的由“五四”和建国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在知识界再次发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陈思和,1996)。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吴良镛,2003)。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反映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给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俞孔坚,2003)。当代中国设计师的责任在于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和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造城市和景观,它们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俞孔坚,2003)。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典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我本人不试图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评论它们,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T型花盆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中卉容器rdquo;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见Pregill and Volkman,1993,p540];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理性、科学、民主和平民化时代的进程,“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2 大视野之二: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Boerschmann,1906)。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去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5号遨游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的欢呼。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希缺。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济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她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身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喜鹊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7%达到65%。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周一星,孟延春,2000;冯健,2003)。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俞孔坚等,2000,2003)。
3 大视野下的理念;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八十五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5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只要认真考察,便不难发现,这种“拆旧建新”恰恰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的封建大一同、非理性、非科学、非民主的反映。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景观建设的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
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一部《城记》(王军,2003),生动地反映了那一代杰出设计学家所经历的可歌可泣的遭遇。
第三,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立体绿化花盆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设计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双孔花盆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 (陈志华,1999)。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也是极其现代的,我们看到的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们决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没有现代建筑精神,它们只有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 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
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拾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经过20多年,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城市和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2001)。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1)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他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古典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2)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之为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俞孔坚,2002)。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4 大视野下的实践:两个参展作品作为对上述理念的实践尝试,我们报送了两个设计项目,非常高兴,它们都被选中参展。
4.1 歧江公园案例
这个案例是讲对被遗忘的和被践踏的人和事物的尊重,重新回到平民,回到土地,回到最朴素的东西。
这个朴素是说50年代建的一个造船厂,90年代破产倒闭了,里面残存着好多破旧的东西,但是这些破旧的东西恰恰记载了我们50年来社会主义工业运动艰辛的历史,记载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和故事(俞孔坚,庞伟,2003)。
这个案例的所在地是广东的中山市,是伟人孙中山诞生的地方,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建伟人的纪念公园,而要建平民的纪念公园,就是我所说的城市设计要回到白话时代,平民的时代,而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说倡导的精神。
这个作品试图重新认识什么是美的,什么是生态的,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历史文化。历史文化不必是几千年古老的历史文化,文化可以在脚下;什么是设计,我说设计可以是不设计,可以是最简单的设计。
这个设计里,我们放弃了所有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国粹的一些东西如曲折幽深的路,而我们这里没有一条路是曲折的;如古典的亭台楼阁,而我们这里面没有用岭南的亭台楼阁。为什么非得用古典的东西才能代表中国呢? 50、30年就为什么不能反映中国。
真正的设计应该解决问题,回到功能,回到用处,回到平民的生活和使用。这个案例中要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包括湖水一天之内有1.1米的水位高差变化,我们设计了一种生态的解决途径,栈桥式的护岸处理,让潮涨潮落,跟大海呼吸相应,所以无论是涨水的、或是落水的,人总是可以亲近自然的。场地中5 0年代破旧的码头也照样记录着当年工人的故事,所以把它保留了,重新再利用。一些破旧的船坞改造了,再利用了;铁轨的再利用,茅草、野草的使用;钢的利用,生锈的钢来自于场地本身的,铁轨的再利用变成日常人们生活的需要,体育锻炼的需要;破旧的龙门吊再利用,变成了入口的门;烟囱的再利用,变成歌颂平 民工作的一个场景;水塔的再利用,其中的一个是通过外罩玻璃变成了一个琥珀灯塔;另一个的创意是剥掉水塔外面的水泥,露出里面的钢筋;通过对旧机器的再利用,使之变成了讲故事的雕塑。设计中大量利用本土野草,我们为什么非得要用贵族化的牡丹和芍药呢?为什么不用这个时代的新的环境伦理来营造新时代的景观,新时代的城市?使用这些乡土物种,是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的化肥、除草剂,不需要任何高投入的管理和养护,是平民化的。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拍婚纱照的最佳场所,每个星期天你都可以看到几对人,十几对人在那儿拍婚纱照。
就是这么普通的景观,里面有普通人的精神、普通人的记忆。红色的盒子记忆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它用了当年工人们居住的宿舍的尺度,很简单,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它是中国的,你可以感到它是中国的,因为这是对中国这一段历史的感觉的表达,它是一种精神的回归,让每一代人重新回到和回味:勤劳的、勇敢的、吃苦的、耐劳的,是平民百姓的精神。
4.2都江堰广场案例
这是个建成的项目。它主要体现回到平民,回到百姓,回到日常人的生活,而要放弃封建意识和一元化的城市广场的形态。这个广场就是平民化的,首先它来源于研究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的建筑语言,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材料。你可以看到它是处处可以亲近的,绝不是巴洛克的,绝不是轴线式的,绝不是一元论的,而是多元的,它可以让民众,让百姓有一个非常亲切、唤起他们的公民性的空间体验。它旨在告诉人们,水实际上是可以设计得与人非常亲近的,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可以做得非常亲切的,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真正休憩的场所,而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巨大而一元化的广场(俞孔坚等,2004)。
结语
早在四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学生就发出了《我们要现代建筑》(蒋维泓,金志强,1956)的呼吁,可惜时代的错误却让他们怀壁其罪。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还他们以公正。“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曾是他们的出发点,景观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景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适宜技术的景观,正是尊重和适应土地及土地上过程的设计,构成城市景观的“白话文”,也是景观和城市特色的源泉(俞孔坚,2003)。设计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无疑是中国现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艰巨而令人激动的任务。